新希望
2025 年 8 月 2 日晚上 7 点,浦东机场。
雷暴雨狠狠敲打着机舱的舷窗,本应该在半小时前就起飞的飞机此时还停留在跑道尽头,机长用广播安抚乘客们焦躁的情绪。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内心忐忑不安,新旅程的第一步就不太顺利。刚才出境时被边检人员拦下的经历让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写有犹他大学的签证和佐治亚理工签发的 I-20 之间的矛盾让他们疑惑。尽管我已经多次确认过相关文件,并且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用旧签证新 I-20 入境的 DP,特朗普这两个月以来想一出是一出的行政操作还是让我惴惴不安。
终于,雨停了,飞机开始滑行。不一会我便置身万里高空之中,雷暴雨消失地无影无踪,新生活正式开始了。
新城市
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了两年时间,却对它知之甚少。如果不算转机时路过的城市,我只去过盐湖城、雪松城和拉斯维加斯三座城市,后两者还是源于同一场旅行。
盐湖城虽然是犹他首府,却并不大,也并不繁华,即使是 downtown 也少有高楼大厦。相比之下,同样作为一州首府的亚特兰大更像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去年申请的时候老师问我是更想去大都市还是小乡村 —— “I don't care”,我回答道。也幸好我没有挑剔学校的地理位置,不然我就真没书读了 —— 佐治亚理工是唯一录取我的学校,而我真的真的真的很讨厌亚特兰大这座大都市。
刚下飞机,甚至还没有出机场,我就闻到了大麻的味道 —— 一种在盐湖城从未出现过的气味。我不知道吸食大麻的人尝到的是什么味道,但大麻燃烧后留下来的余味怎么也不像是一种享受。直到在亚特兰大待了几个月、坐了一两百次地铁,我才逐渐习惯这种气味。
有大麻味道的地方就一定有大量的 homeless,治安也不会太好,这是美国大城市的通病,而亚特兰大位由于众所周知但众所不能说的原因,治安问题尤其突出。如果你在亚特兰大坐地铁,遇到流浪汉的概率是百分之一百。各大超市的停车场也时常聚集着游手好闲的人。不过流浪汉本身倒不是特别危险,遇到了直接无视即可,听说我的朋友曾经在学校附近见到过 drug dealing,那才是真可怕。刚来的两个月,我不敢在天黑之后出门,但因监考晚场考试而在八点后坐了几次地铁后,我发现夜晚的地铁也没有想象中的危险,胆子就越来越大了。
当然,大城市也有大城市的好处:它更热闹。亚特兰大的各种演唱会、演奏会、歌舞剧、脱口秀表演比盐湖城多了不少 —— 可它们似乎与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是一个很宅的人,对我来说所有演唱会的消息加起来也没有《丝之歌》的发售日期重要,况且这些活动大多在 downtown,而 downtown 又很危险。除去这些文化活动,亚特兰大这座城市本身也没有太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 一个把“可口可乐博物馆”写到城市介绍里面的城市能有多有趣?当然这也不怪它,因为整个美国都没有什么值得探索的地方。有一次,我和办公室里坐我边上的俄罗斯人闲聊,她评价道:“The cities in the U.S. are empty”,相比之下,欧洲的城市似乎更有趣一些。
在来亚特兰大之前,我就听许多人说过亚城的气候和中国南方很像,不会有盐湖城那么多的雪。好吧,没雪就没雪吧。可我没意识到的是,亚特兰大温暖湿润的气候竟会带来这么多虫子。似乎不论我怎么努力灭虫,在家里伏案工作时总能看到一两只会飞的小虫子停在我的台灯上,只有入冬以来骤降的气温可以彻底消灭他们。亚特兰大的冬天没有盐湖城那么冷,但零下的温度也是常见的,出门在外不戴顶毡帽容易把耳朵冻伤。在亚特兰大待地越久,我就越觉得这座城市的气候很像那座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 —— 只是没有那么多雨。我曾向我的外国朋友介绍杭州,说中国人认为它是 "heaven on earth",但我会很快地补上一句:"I'd rather go to hell if that's true"。
所以,当代数几何的老师(很巧的是,他跟我同时从犹他大学转到了佐治亚理工)问我是否想念盐湖城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
"Oh I wouldn't lie. I was already missing SLC on day 1 here..."
新学校
尽管我不享受亚特兰大的热闹,却很喜欢佐治亚理工的活力。
当我还在犹他的时候,周末也时常会去学校转转,可犹他的校园总是静悄悄的,即使是橄榄球赛,也只有体育馆附近很热闹。而佐治亚理工给我的感觉却是每个周末都有各种活动,Tech Green 永远是人来人往的。这让我想起了本科跨校区上课的经历:玉泉总是死气沉沉的,路上遇到的都是黑衣黑裤黑跑鞋的工科老博;而紫金港则活力满满,随处可见活蹦乱跳的本科生。尽管我遇到的大部分美国人都非常热情(至少他们表现得非常热情),但也许在美国的不同学校,文化差异也是蛮大的。人们说南方有所谓的 "southern hospitality",这里的人们似乎比我在盐湖城遇到的更热情、更有礼貌,这也让我不得不更有礼貌:口语课的老师多次提醒我们,在这里哪怕是跟学生说话,也一定要多说 please,否则就会被视作一种侮辱。
就本科生群体而言,佐治亚理工的中国人要比犹他大学多得多,我在犹他当助教的时候,接触过百来个本科生,几乎没有中国学生,倒是越南人很多。而在佐治亚理工,我三十来人的 studio session 就有三个中国人。我想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佐治亚理工是一个排名更靠前的学校。如今 CS 大热,而 GT 的 CS 又普遍被认为是四大之下的第一梯队,来这里学 CS 的中国人自然就很多。
庞大的工科让 GT 的校园风气呈现出浓浓的 Geek / Nerd 感 —— 在 GT,各种群体竟然是用 discord 来组织的。与此同时,人数众多的工科学生产生了更多的数学 TA 岗位,所以 GT 的数学系也比一般的学校要大不少 —— 至少比犹他要大多了。对我来说这挺好的,因为我还在探索自己究竟要干什么,一个大一点的数学系能够提供更多的选项。与此同时,GT 的数学系有非常多和其他工科院系的合作,除了 Math Ph.D. 这个项目之外,还有诸如 CSE、ML、QBios 的 Ph.D. 项目也会设在数学系下。
GT 数学系里的华人依旧不多,且集中在应用数学和 PDE 这两个方向,我的中国同学们也大都是他们的学生。这可能和国内一直以来重分析、轻代数的培养模式有关 —— 即使我没有上过分析方向的研究生课,这里研究生 Analysis I 和 II 学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包含在浙大本科的实变和泛函之中的。犹他和 GT 数学系的氛围是完全不同的。犹他的代数非常强,所以能够开出更加全面的代数课程,比如交换代数、同调代数和复几何在犹他基本上每年都有。而在 GT 数学系,往年的代数几何 2 都不一定讲 Scheme Theory,而是讲 Tropical Geometry 之类的更加实用的东西 —— 毕竟 GT 的强项是 combinatorics。在犹他,我遇到的十个数学 PhD 可能有九个在做代数几何,路边的本科生也能熟练地使用 exact sequence,而在 GT,当你在 algebra seminar 找个位置坐下,却听到大家都在谈论 matroid theory。
新朋友
计算机系的同学似乎是千篇一律的,戴眼镜、二次元、格子衬衫冲锋衣。而我在数学系认识的人则更加多样化一点。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是一路学数学上来的,但也有一些 outlier,比如之前学文学的、在 Google 写代码的,甚至还有一个哥们以前是申花青训的足球运动员。在遇到我之前,系里的其他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是 nerd,而在遇到我之后,他们觉得我才是 nerd。的确,他们的现实生活要比我充实的多。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比我更年轻的原因。过去那些犹他的同事们平均比我大三四岁,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和比我年长的人打交道。如今我成为了朋友中最为年长的人。当我还在适应这一新身份时,对我的称呼已经悄然转变。我姓龙,这个奇怪的姓氏让我从小到大的外号都围绕它而产生:龙仔 -> 龙爷 -> 龙神。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叫过我“龙哥” —— 直到现在。我不禁想起,我的父亲刚刚工作的时候也常常被人叫做“龙哥”,这同样是因为他曲折的职业生涯让他比同事们年长不少。
和年轻人做朋友是一件好事,它让你以为自己还没老。在犹他的时候,我和朋友们谈论着工资、房、车和彩礼,而如今我和朋友们则谈论数学、八卦和网络烂梗。我时常有一种错觉:两年前我开始读博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了,而现在我依旧是博一,却回到了二十三岁。时间是个奇妙的东西,它并不总是线性地流逝。
由于数学系松散的行政结构,认识其他人既变得困难、又变得容易了。一方面,数学系的课题组没有工科课题组那么有组织有纪律,更多时候仅仅是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单线联系,学生和学生(尤其是新生)之间很难建立稳定的、频繁的联系;而另一方面,正因为没有课题组的存在,数学系的学生们平均地分散在各个办公室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机会反而变多了 —— 而且数学系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比如每天下午的 tea time。所以,除了那些不论在哪里都能抱团的中国人之外,我也有幸在这个学期里结识了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在那些外国朋友中,与我交流最为频繁的是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小哥 Julian,我与他聊天的频率甚至远超我和其他中国人。Julian 时常跟我抱怨,他的幽默感在来到美国之后逊色了不少,因为许多西班牙语的笑话并不能翻译成英语,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 Julian 是个风趣的人。我们的英语说得都不算好,听懂彼此的意思倒是不成问题,我们就这样用蹩脚的英语开着玩笑,也能带来不少欢乐。虽然我和 Julian 这学期有两门共同的课,但我第一次和他聊天却是在学院的 tea time。我了解到,在读 PhD 之前,Julian 曾经在公司里上过两年班,对深度学习共同的讨厌很快让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他教会我西班牙语中 rolling r 的技巧(我现在终于能发出这个声音了,虽然把它放在句子里还是不太熟练),而我告诉他中文中音调的读法;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去健身房举铁,而我跟他分享做中国菜的万能公式;他向我叙述他过去约会的经历,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他我对女生一无所知。他常说 Columbia 是个贫穷的国家,并觉得我的中国朋友们都是 billionaire,我才发现我和他确实有不少共同的气质:从来不换的鞋子,为数不多循环使用的外套 —— 当然,哥伦比亚人是不穿冬装的,当我穿着大衣围着围巾却还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他却淡定自若地穿着短袖。Julian 是我见过最 chill 的人,他不止一次地邀请我和他同去学校的拉丁舞俱乐部学习 salsa 和 cha-cha,和我周围刻苦努力的中国同学相比,他似乎更加享受慢节奏的生活。每次和他聊完,我都觉得自己轻松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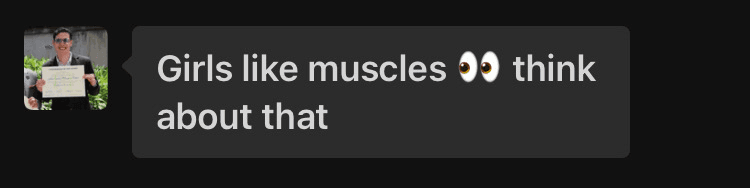
另一个和我经常聊天的人是办公室的同事 John,谁能想到拥有这么平平无奇的名字的竟然是一个大胡子希腊人!John 不仅在数学上颇有天赋(他读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在 delayed equation 领域发表了不少结果了),对语言学的掌握也令人惊奇。他来自克里特岛,在巴黎上大学,因此除了自己的母语希腊语,他也精通法语。他用业余时间自学了瑞典语和德语,还翻译了一些瑞典语的古籍。毕业后在台大交换的经历让他甚至会一点中文 —— 至少他能听懂不少闽南语,这就比我还强了。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跟我骄傲地展示自己手臂上的中文纹身 —— 那是两个歪歪扭扭的汉字“姑姑”。他向我解释在希腊人们并不用“你妈的”骂人,而是说“你姑姑的”,而他觉得“姑姑”的发音怪有意思的。我突然想到我在《刺客信条:奥德赛》中学到的唯一一句希腊语 "Malaka",但出乎我的意料的是,John 告诉我这个词虽然有骂人的意思,平常好朋友之间也喜欢互相用它来称呼。
John 强大的语言能力已经足够让我羡慕了,让我更加惊讶的是,他本科的前两年并不在学数学,而是在学哲学,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世界有很多困惑,而哲学能够解答这些困惑。
"Did you find your answers in Philosophy?"我问他。
"No."
"Well, I once attended a seminar on The Republic by Plato at the age of 19. The book is like a bible to me."
"Bro, I mean, how could you tolerate it? The book is so boring."
我时常觉得 John 的人生才算真正的人生,而我只是麻木地活着。
除了这两位经常聊天的朋友,还有不少外国朋友在我刚刚来到数学系的时候热情地欢迎了我。Daniel,一个非常健谈的在美国长大的韩裔,在我搬进办公室的第一天就主动跟我聊天,告诉了我 GT 数学系的各种内部消息。他领导了数学系的不少学生组织,业余时间还在 GT 的俱乐部里做脱口秀表演。同时他也是电子游戏狂热爱好者 —— 不过我用比他更短的时间打通了《丝之歌》,可能是因为我暑假里刚刚通过《空洞骑士》的五门挑战,手感尚在。由于 Daniel 同样是做代数的,我们以后估计还会经常遇到;Kseniia,办公室里坐在我边上的俄罗斯女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人 —— 美国有许多带着斯拉夫姓氏但却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人,我并不把他们归作俄罗斯人,即使他们中有的甚至拥有俄罗斯国籍。俄罗斯和中国都从苏联继承了不少东西,在和 Kseniia 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俄罗斯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和我们有不少共同点,甚至她本人也参加过高中生物理竞赛。更有意思的是,Kseniia 本科学的也不是数学,而是软件工程,如今她正在 GT 数学系的 QBios 项目下面做一些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还有在 tea time 经常碰到的几位朋友,如果没有他们我每次去喝茶都得孤零零地站着,学期初的时候曾有一位朋友邀请我去她的生日聚会,只可惜时间太晚,而我又不住在学校附近,最终只好作罢,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们能够欢迎我这样一个外来者,我注意到系里的中国人一般并不会和外国人一起玩。
在申请数学系的日子里,我曾认定人是孤独的,世界上不可能有人真正地理解我。如今我虽然依旧这么认为,但也渐渐意识到朋友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那几位挚友一路以来在精神上提供的支持,我可能早就放弃了。我期待着未来的所有遇见。
新专业
我并不是系里面唯一从计算机转到数学系的,双专业在美国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但我可能是在计算机系待的时间最久、接触编程时间最长的人。就博士生而言,数学系的生活和计算机系的生活天差地别。
数学系的博士新生由委员会统一录取,因此从名义上并没有固定的导师 —— 虽然大部分人都提前联系了系里面的老师。系里面给我分配的 initial advisor 是一个非常佛系的乌克兰人 Anton。我在学期初的时候和他 meeting 了一次,之前听说斯拉夫语系的人说话都很难听懂,可理解他说的话却并不困难,因为他总是慢条斯理的。Anton 的研究方向是 computational algebraic geometry,但他兴趣广泛,似乎系里面所有跟计算代数相关的研究他都懂一些 —— 听说他打桥牌也是好手,之前还在数学系里面组织过桥牌俱乐部。
由于我刚刚从计算机系转过来,对自己想做的事情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第一学期并没有马上开始跟 Anton 做项目,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上课上。除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必修课(ethnic training, oral English training, TA training etc.)之外,这学期我一共上了三门数学课:代数几何、微分拓扑和 Matroid Theory。
美国的代数几何基本上都是分为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围绕 variety over algebraically closed fields 讲古典代数几何,对应 Hartshorne 的第一章,而第二学期讲 Scheme Theory,对应 Hartshorne 的二三两章。虽说 Hartshorne 是代数几何圣经,这本书其实现在来看也有点过时了,且并不适合自学,因此我们用的教材是 Garthmann 的讲义,个人感觉它写的比 Hartshorne 的第一章要好,因为它在 projective variety 之前就引入了一般的 variety 的概念,这让读者能够更好地将 variety 和流形相类比 —— 不论是 Hartshorne 还是 Fulton,对 projective variety 的引入都是缺乏动机的。很巧的是,今年教代数几何的老师是 Harold,他刚刚从犹他大学跳槽到佐治亚理工,而我在今年的春学期还上过他在犹他大学开的代数拓扑课(没错,犹他大学的代数拓扑课是代数老师教的)。在课后我问他是否有空带我读 Hartshorne,他也慷慨地答应了。
代数几何的期末作业是写一篇课程论文。由于我觉得自己目前学的东西还不足以支持我看懂前沿的东西,所以我打算从另一方向探索一下我的兴趣,等到代数几何 2 的课程论文再写一些更抽象的东西。我最终选择了数值代数几何(numerical algebraic geometry)这个主题,这也是 Anton 的研究方向之一。数值代数几何的一切算法都依赖于多项式方程的求根,求解多项式方程最常见的方法是 homotopy continuation,而 homotopy continuation 的理论依据则是 the parameter continuation theorem(PCT):它说明当多项式方程组的参数在一个“一般”的范围内发生变化时,其根的数量保持不变。有许多证明 PCT 的方法,目前我读到过的最简单的方法用到了 Groebner basis,这就构成了我期末论文的主要部分。不过,当后来我问 Anton 时,他跟我说用 Groebner basis 来证明 PCT 依旧是 overkill,应该还有更简单的做法。
微分拓扑其实就是国内的微分流形课。我选这门课主要是为了拓扑的 comp exam 做准备,因为我之前在犹他已经上过代数拓扑了。这门课的老师是 John Etnyre,他是低维拓扑领域的大牛,ICM 2026 的一小时 speaker,他的学生毕业之后都去了非常厉害的学校做 postdoc。John 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聪明人,他讲课的语速很快,回答问题的语速也很快。如果课前完全不预习的话,一定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然而微分拓扑这门课给我的感觉就是自己把内容推一遍就一定能搞懂,而如果不自己推一遍光靠别人讲是无论如何都有细节不清楚的。
高中搞竞赛的时候我就听说过 matroid,它是保证类似 Kruskal 的贪心算法正确性的离散结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过更多数学训练的缘故,如今的我再上 matroid theory 的课就觉得之前看的那些基于 matroid 的证明也没有那么烧脑了。这门课的老师是 Matt,他不仅是一个数学家,还是一个魔术师,办公室门上常年贴着一张他的魔术表演的海报。这门课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传统的 matroid 理论,包括它和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的联系 —— Jack Edmond 的工作;二是 representation over tracts and pastures,这是 Matt 自己的工作,通过将 matroid 的表示扩展到比 field 更为一般的代数结构上,他们成功地统一了关于 orientable matroid、valuation matroid 的研究,并且将 matroid 的表示问题规约到寻找 pasture 之间的 morphism ——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果,因为它把难以处理的 matroid 变成了容易处理的代数结构;最后一部分是 combinatorial Hodge theory,这是 June Huh 的工作,可惜我虽然能够 follow 那些证明的步骤,却很难说我真的听懂了,大概是因为我不了解 Hodge theory,所以不知道那些数学技术的动机是什么。
由于 Matroid theory 是一个 special topics course,它并没有非常严格的考核机制,我们的平时作业都是同学批的,到学期末的时候应该每个人都拿到了 A。期末的作业也是写论文,在 Matt 的建议下,我选择了一个和 TCS 结合的问题:Matroid basis counting。如果具体到图论中,这就是生成森林计数。人们已经知道这一问题是 NP-hard 的,因此我所阅读的论文提出的是一个近似算法 —— 但它也已经接近理论上最佳的近似算法了。其核心技巧是将 basis counting 转化为 matroid polytope 上的优化问题,而后者可以凸优化算法被高效地解决。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我写的期末论文,或者直接读原论文(说实话,我觉得原文已经写得非常浅显易懂了,也不涉及什么高深的数学,这就让我的报告显得有些无意义……)
Matroid theory 这门课还附赠了一个宝贵的机会:由于 Matt 本人是 June Huh 的好朋友,当 June 在九月份访问 GT 的时候,Matt 邀请我们和他在 matroid theory 的教室里共进午餐 —— 我想想我这辈子估计也没有多少和菲尔兹奖得主一起吃饭的经历了。人们总说 June 大器晚成,因为他很晚才开始学数学,而且也并没有 follow 一般人学数学的路径 —— 据他自己在吃饭的时候说,他从来没有刷过 Hartshorne 上面的题目。但 June 的天才气质却是无法掩盖的,他说话不紧不慢,却总是能直击问题的要点,在向我这样啥也不懂的研究生解释前沿的工作时,他也能做到浅显易懂。后来当 June 在报告厅做学术报告的时候,就连过道上也坐满了人,而前排全是系里的教授 —— He is such a rock st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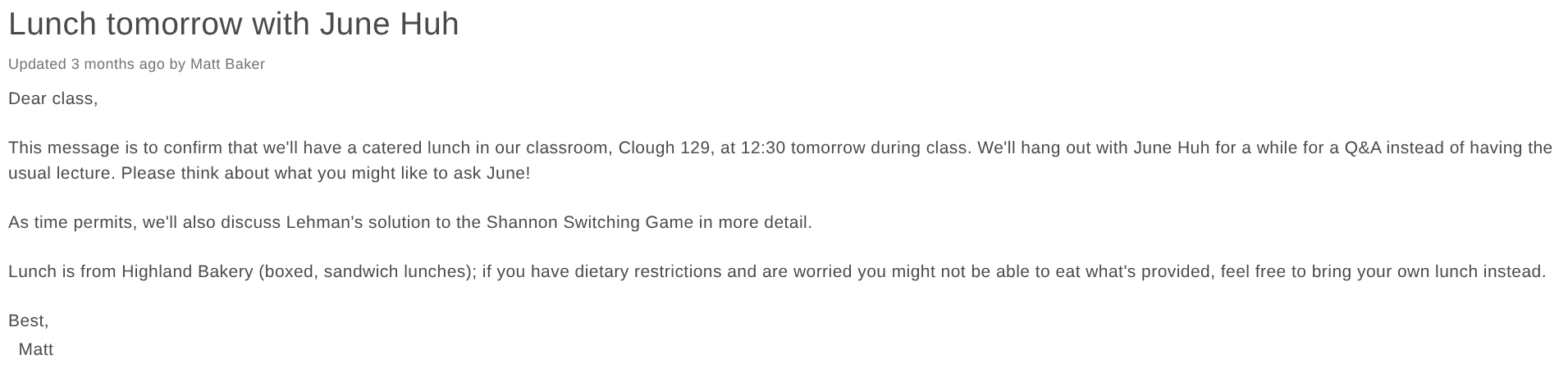
除去数学课上和老师们的交流之外,由于这学期上的口语课布置的作业,我有幸采访了一位学校里的新老师 Julia。Julia 做的东西很有意思,她称自己为 applied algebraist,而 applied algebra 是一个小众的领域(其实美国前面的学校除了 GT 我也没怎么见过 applied algebra 的研究)。她和我讲了一个她之前的工作:在统计学中,人们往往需要用几个 gaussian 的 mixture 来拟合一个概率分布,其中 method of moments 是一种无偏的估计方法,它通过拟合数据的 moments 来确定 gaussian 的参数。这就带来了一个自然的问题:我们需要多少阶 moment 才能完全确定所有 gaussian 的参数?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多项式方程求根的问题(如果考虑到噪声的存在,求根问题就变成了优化问题)Julia 在 Madison 读博的时候给出了一个比统计学中结论更强的 bound —— 前提是数据的分布足够“一般”,她和合作者的研究给 method of moments 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来到数学系之前,我曾日日夜夜幻想这里的生活。如今我已经在数学系待了一个学期了,我觉得这的确是我梦想中的生活。
新身份
数学系的博士生有两重身份,他们既是蹒跚学步(虽然我周围的一些同学已经起飞了)的学徒,同时也是为本科生指点迷津的老师。和别的系的 TA 只需要答疑、批作业不同,数学系的 TA 需要真正站上讲台讲习题课。
我想做一个好 TA,认真备课,认真讲课。但效果似乎适得其反,我犯了一个第一学期 TA 常犯的错误:我讲的太难了。我是线性代数的 TA,因此我也希望用当初我的老师教我线性代数的方法去教我的学生,毕竟我也曾是工科生。然而我很快就发现美国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好的学生不用我讲也能很快把题目做出来,而相对落后的学生则似乎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这让我颇为不解,毕竟我已经把解题的每一步都尽可能详细地展开了,板书的内容甚至比教材上的证明都要更加事无巨细,如果他们连这也理解不了的话,又怎么理解教材上的内容呢?直到学期过半,我才因为在吃饭时和教这门课的博后大哥聊天而知晓了缘由:
"So, you never proved anything in your lectures?" 我惊讶地问道。
"If the proof is only one or two lines, then I will prove it for my students, otherwise no."
"Then how do you explain those true and false questions? I mean if the statement were true, you have to prove it, right?"
"I will give them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correctness."
"I see, so this is a belief-based course instead of a proof-based course..."
我很纠结,一方面,我不希望我的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另一方面,学校似乎不要求学生知其所以然,所以我的学生们往往并不想要把线性代数搞懂。一个学期下来,我还是不知道这门课到底应该怎么教。除了判断题之外,还有一些题目会问你 "Is XXX possible?" 或者 "Construct an example for XXX",我去听别的 TA 上课,发现他们并不讲自己是如何得到这些例子或者反例的,但我真心希望能够把我构造这些例子的思路告诉我的学生们,这需要学生至少对数理逻辑有一定的熟练度 —— 而我的大部分学生在这方面都有所欠缺。最终的结果就是,当我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只有最厉害的几个本科生能跟上我的思路,以至于到学期末的时候,来听我上课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 而那些来的人是最不需要来的,他们自己也能把线性代数学明白。从 TA 的角度来看,我是颇为失败的。我很想建议学院以后不要安排国际博士新生教 1 开头的课,毕竟我的学生们大多也是刚到 GT,碰上我这么个 TA 也挺倒霉的 —— 我本人有幸在大学第一学期遇到了非常好的线代和微积分老师,他们给我的大学生活开了一个好头。
事已至此,希望下学期的我能够更好地找到难度和数学上准确性的平衡点吧。
当然,我的学生们还是很可爱的,他们时常让我想起本科时那个精力充沛的自己。由于我的 studio session 在早上的八点半,一般来说并没有什么人提早到,如果有,我会和他们聊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尽管我的学生们学的专业大差不差,大都是 CS / CSE / ECE,可他们这学期选的课却大相径庭,Java、大学物理、概统、离散数学……学啥的都有。美国本科的培养方案相比国内更加自由,必修的课程非常少,所以大部分人为了满足毕业的学分要求都会修双专业或者选研究生课程。而只要考过了 AP,大部分课的预修要求也能满足,不一定非得按照某个顺序来上。除了这些专业课,他们还告诉我美国的本科生也要上诸如美国历史之类的人文课 —— 谁说美国没有思政教育的来着?
佐治亚理工的考试喜欢安排在晚上,而且一考就是两三个小时,监考是非常无聊的。看着这些奋笔疾书的学生,我时常想到刚读本科的我,那竟然已经是六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的我能够预料到今天吗?我不知道。在上完最后一节课之后,有一位中国女生询问我关于研究生申请的事情,我笑了笑,说现在研究这个为时尚早,也许过一段时间你才会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还是先好好享受你的本科生活吧!